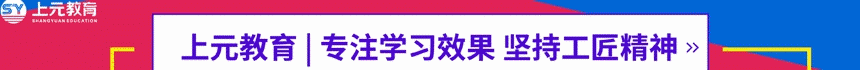“你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在给一个幼儿园的孩子讲课。”广州民办小学黄石小学校长黄胜文在会议室里坐定,为了吸引生源,他每周要抽一个下午到附近社区的幼儿园,或者把幼儿园的孩子请到学校,让孩子和家长们提前坐进小学教室里“试听”,每次他要讲课,宣传办学理念,企图招徕这些孩子进他的学校。现在他的学校有600名学生。
黄胜文有15年教学经验,1995年大学毕业后,在湖南老家一个县郊区的公立小学当了一年地理和数学老师,每月400元工资,看到同乡到广东打工能挣一千多元,便辞职到广州“改善生活”。他被招进一家集团做工,没有想到这个集团原来还办学校,他很快回到了教师本行。
1997年黄胜文在广州加入民办教育行业,先在民办学校教了3年小学数学,先后负责学校的德育,学生管理工作,少先队工作,校长助理,副校长等职位。5年前被集团派到位于广州市另一区域的一所“国有民办”小学做校长。所谓“国有”是1996初办时由政府建了校舍,由集团自行按照教育局指引和办学标准进行独立自主办学,集团要按照国家政策免费承担起社区居民子女的义务教育职责,对没有户口的学生实施物价审批的收费教育。
在两种学校都工作过的黄胜文,感受到两者的区别:公立学校的老师只要专注于专业教学就可以了,民办教育工作者,有时是教师,有时是“促销”,有时是“法官”,有时是“咨询师”,有时是“服务员”……
“说白了,民办学校里的学生和家长就是客户。”黄胜文说,“我经常给老师们说,你做好老师,就等于每年为集团省10万元宣传费。”
“做”了一屋子的表格、文件、数据
“今天上午我为几个学生的学籍的事跟教育局的人又吵了起来。明天上午我还得去跑学籍,都跑了好多趟了。”黄胜文经常要为学生跑“学籍”,户口不在本地,就没有学籍,没有学籍就不能考初中,如果是在私立中学上的初中,考高中也要学籍。过去没有户口民办学校可以上,现在不让上了。“有的孩子是‘二奶’生的,有些是超生的,没有户口,就不给学籍,没有学籍就意味着民办学校对孩子的教育服务行业是非法的!难道他不是中国人吗?难道明天让他上大街上放手榴弹,或者让这个孩子天天在家里玩儿算了。如果我是家长,我会不停上诉。”黄胜文说,很多民办学校校长讲起学籍的事情都很窝火,“为什么人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就丧失了受教育的公民权利呢?”
黄胜文觉得民办学校在整个社会管理体系中,是被当成一个私人工厂来管理的。“即使民办学校的办学者要获得合法利润,那也是通过提供让家长和社会满意的教育服务来实现的啊,行政管理部门不能因为民办学校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就一辊子打死啊。”
除了教育部门“正当”而“例行”的检查外,作为校长,他每天穷于应付的主要是其他政府机构的检查。每次来人检查,黄胜文都要提前准备好汇报材料,他称这些是“陪政府玩的小游戏”。“天天逼着学生回去拿父母的工作证、身份证、户口本、计划生育证,学生都快被赶跑了。”
黄胜文为了应付检查,三分之一的精力花在“做”各种表格、文件、数据上。有一年为了评“区级学校”,他和老师加班加点填写的各种表格和档案材料整整占了一间房子,到现在还存放着,其实也没有人看。对民办学校来说,“区级”已经到头了,旁边农村小学也是个“市级”。
民办教育户籍换学籍的硬指标,是否会影响公平教育?
两张不同的课程表
下午4:40,几辆黄绿色的校车鱼贯开出校园。“放学了。”黄胜文扭头看着窗外说。这里的学生比公办学校的学生放学晚一个小时。教师没有专门的办公室,办公桌就放在每个教室的后面,学生有问题随时可以问老师。
其中一辆校车上坐着四年级二班的李筱伊,家离学校有三四站路。5点一刻,她到家后,花一个小时做剩下的作业,花半个小时练小提琴。
李筱伊从一年级开始学古筝,每周五下午学两节课,后来她又选择了周四下午的萨克斯课。受到音乐的感染,二年级时她主动提出想学小提琴,家长就带她到少年宫参加了一个小提琴班。她说她长大想当音乐家。现在她会弹一曲瑶族舞曲,曾在学校表演过。
“艺术教育是我们学校的特色。”黄胜文说,但为了坚持艺术教育,他得跟教育部门玩“躲猫猫”。
黄石小学让每个孩子都至少选学从小提琴到古筝的14种中西乐器中的一种,请广东民乐团和大学里的器乐教授来教课,每周音乐课的总时数已达4节,10%的学生同时在校外还请音乐家教。国家课程体系规定一周必须上两节国家规定教材的音乐课,黄石小学的这4节乐器课不算规定的“音乐课”,教育局的检查显示不合格。艺术课程是这样,其他各科也同样。
课程体系规定小学5年级每周英语课4节,因为是“小班制”教学,黄胜文认为有的班3节课就可以了,而有的班因为某个学期转学生多,转来的学生以前没有学过英语,就需要增加一节课。但教育局认为这是不行的。
课程系统对于节数和门数都规定得十分僵化。增加了,就是加重学生负担,没有落实素质教育;减少了,也是不符合课时数的要求。
对于语文课,广州市规定五年级一律每周5节课。黄胜文想根据实际情况在不同班级之间做些微小的调配,觉得薄弱班级需要六节才能达到标准,而优质班级其实只需要3节。但他并没有这种权力。
黄胜文觉得语文课本就20多篇文章,分析来分析去,还不如让小孩看一本童话故事。他们开列中外经典书单,让家长和学生一起读书。说着,黄胜文指了指旁边书架里堆着的一大摞推荐阅读的书。
他认为像数学、英语、语文、艺术、体育,国家只要出一个整体的目标,一年级要掌握多少字、哪些语法、写哪些文章,学期结束你针对这些学校测试,看是否达到基本目标,至于用哪本书教、开了多少课我不管你。
还有很多标准课程体系不允许的内容:思想品德课如果换一种另外的形式来教,比如学校请了礼仪大师来授课,不允许;“德育”除了爱祖国之外其实更强调的是“生活教育”,不允许。
黄胜文学会了“阳奉阴违”:“我们有两张课程表,一张是自己用的,一张是给教育局看的。”
民办学校更看重分数
其实想当音乐家的李筱伊到五年级下半学期以后,在黄石小学将再也不能上她喜欢的古筝和萨克斯课了,为了升学率,学生的艺术教育到六年级的时候全部停下来,要冲刺升初中。“我们在一二三年级比较重视孩子玩得开心,到四年级以上就会慢慢侧重到应对考试上面。”黄胜文说。
压力不是来自集团和教育局,而是来自“家长的考核”。
黄石小学吸引家长的招牌是培养“个性外向的领袖型人材”,平时学生按照社团模式自我管理校园。李筱伊就在学校担任中队长职务。但学校规定,学生自我管理体系也在五年级后一律戛然而止,那时候,李筱伊会和同年级其他所有的学生干部集体“被卸任”、“被退休”,从而集中精力应对考试。
黄胜文理解的“教育”是:20年后,从这个学校出来的学生还带有共同的品质和气质。但没有家长会看二十年后的素质,他们只能看到眼前的考试成绩。不管你说的天花乱坠,最后比的还是考试成绩。黄胜文说他就在这种夹缝中“戴着脚镣跳舞”:又要花样翻新让家长看到“素质”,又要最后升学时学生考得好皆大欢喜。
“民办教育比公办教育对考试更看重,考分高,是民办学校招生的一张王牌。”黄胜文说。
为了提供这种“教育服务”,老师得和校长一起挑起这不轻的担子。教师的平均工资才不到2000元,只有公立学校老师待遇的三分之一,怎么留住人才呢?“靠事业、靠感情留人。”黄胜文说得并不自信。
穿着校服、戴着红领巾,和所有公立学校毫无二致的孩子们放学后,已经有十六年楼龄的教学楼显得老旧、空荡、幽静。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4108